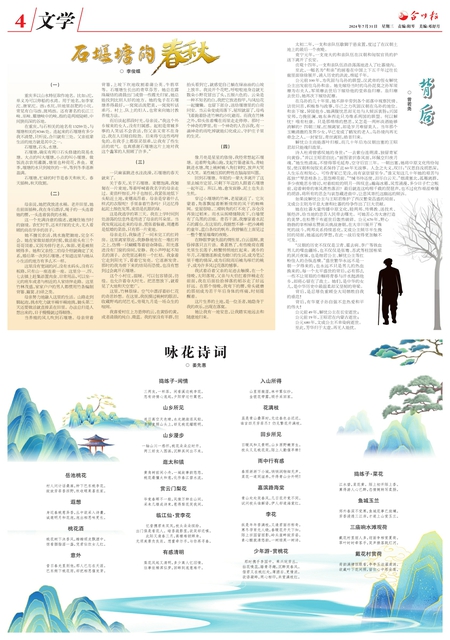(一)
重庆多以山水特征取作地名。比如:沱,单义为可以停船的水湾。用于地名,如李家沱、唐家沱。凼:水坑,田地里沤肥的小坑。常见有白马凼、斑鸠凼。还有著名的长江三峡、巫峡、瞿塘峡中的峡,指的是两坡陡峭、中间狭而深的谷地。
在重庆,与石相关的地名有13259处,与堰塘相关的8346处。连起来的石堰塘有多少我不清楚,只听说,合川就有三处。父亲祖辈生活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。
石堰塘,石头,水塘。
石堰塘,确实有两口石头修建的简易水塘。大点的叫大堰塘,小点的叫小堰塘。做饭洗衣农用灌溉,塘里也种荷花,养鱼。夏季,堰塘的水只到坡坎的一半,等到冬季逐渐盈满。
石堰塘,忙碌的时节是春天和秋天。春天插秧,秋天收割。
(二)
母亲说,她把我放进水桶。老井田里,她在前面插秧,我在身后漂浮,绳子的一头连着她的腰,一头连着装我的水桶。
这一个充满诗意的描述,遮掩住她当时的窘境。农忙时节,还未归家的丈夫,无人看顾的尚在学步的孩子。
她不擅长农活,挑水施肥锄地,完全不会。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,做活前头有三个哥哥顶着,又因为排行老幺,体弱,更是被照顾得多。她和父亲经二伯母介绍就确定了关系,婚后第一次到石堰塘,才知道这里与她从小生活的地方有多么不一样。
这里没有宽阔的河,没有水码头,没有石板路,只有山一座连着一座。这里分一、四、七去镇上赶集添置肉食、日常用品,可以坐一元的班车或者与相近的人家结伴走路。这里竹林茂盛,家家户户的男人都惯用竹条编制背篓、簸箕、扫帚之类。
母亲努力地融入这里的生活。山路走到脚起泡,挑水吃力就半桶半桶地挑,锄头第二天还要做活就直接丢在田里。办法总归是人想出来的,日子慢慢就过得顺络。
当养殖的风儿吹到石堰塘。母亲背着背篓,上坡下坎地收割着蒲公英、牛筋草等。石堰塘生长出的青草芬芳。她总在露珠凝结的清晨出门或借一些霞光归家,她总能找到比别人好的地方。她的兔子在石堰塘养得最好,一窝窝活泼肥美,一窝窝听话乖巧。村上、队上的妇人,也常来向她讨教养殖方法。
而后谈起那段时光,母亲说,“我这个外乡嫁来的女人,没有归属感。起初是常被多事的人笑话不会农活,你父亲又常不在身边,我在人后暗自较劲。后来得亏这些鸡呀兔的,在我手上都很灵很乖,让我有了些生活的底气。也真感谢石堰塘这片土地对我这个蠢笨的人照顾了许多。”
(三)
一只麻雀跳进水洼洗澡,石堰塘的春天就来了。
关于春天,关于石堰塘。麦穗饱满,我匍匐在一片麦地,等着呼喊着我名字的母亲走过。麦苗杆细长,叶子也细长,我紧张地低下头贴近土地,麦穗高昂着。母亲是穿着什么样式的衣服呢?手里拿着竹条吗?只还忆得起泥土颜色发黑,麦苗是扎眼的绿。
这是我逃学的第三天。我在上学时间到处游荡的信息终是传进了母亲的耳朵里。当我发现远远走来的母亲,慌张着躲避,周遭都是低矮的菜苗,只有那一片麦地。
母亲走后,我躲进了一间未完工的红砖房。这里离家很近,我静静地坐在一堆红砖之上,仿佛一只蝴蝶等着宿命降临。阳光落进没有门窗的房间,安静。我小声哼起不知名的调子。衣兜里还剩有一个红桔。我拿着它走到阳光下,看着它发亮。它逐渐发烫。那时的我为接下来的结局而恐慌,也没有想到过会离开石堰塘。
这个小村庄,温暖。可以包容错误,彷徨。也允许着夸大时光。把思想放下,就看见了大地和天空宽广。
这里,竹林很绿。空气中漂浮着砂仁花的奇思妙想。在这里,我抚摸过桃树的眼泪,收藏野鸡的尾巴毛,旁观九月是一场众生的喧闹。
我喜爱村庄上方悬停的云,在黄昏的黄,或者清晨的纯白、微蓝。我的家没有羊群,但抬头看到它,就感觉自己躺在绿油油的山坡上放羊。我说开个花吧,呼啦啦地身边就无数朵小野花冒出了头,五颜六色的。云朵是一种不知名的白,我把它放进指甲,与凤仙花一起慵懒。也留下部分,送给堰塘里的白荷问安。当云朵变成雨落下,屋坝就湿了,母鸡飞着跑着卧进竹林的沙坑避雨。而我在竹林之外,仰头张着嘴在雨里走走停停。那时一个神奇的梦里,有一个神奇的人告诉我,有一滴神奇的雨吃掉就能幻化成云,守护庄子里的生灵。
(四)
像月亮是星星的依傍,我经常想起石堰塘。追着野兔满山跑,支起竹篓逮雀鸟,青蛙跳进水塘,爬上桃树被八角钉刺咬,放声大哭又大笑。某些被压抑的野性在脑海里叫嚣。
回到石堰塘。年轻的一辈大多离开了这里去城市定居,只剩下年迈的人跟着石堰塘一起年迈。所以,她,愈发寂静,泥土也失去生机。
穿过小堰塘的竹林,老屋就近了。它灰蒙着,角落飘摇着断断续续的风干的蜘蛛网。堂屋很暗,二楼转角的灯不亮了,谷仓没再装过稻米。雨水从阁楼缝隙流下,白墙便有了乌黑的泪痕。青苔干涸,我摩挲着水泥石的露台,在这里的,我臆想不够一把沙滩椅的童年,蓝白条纹的帆布,我曾躺在上面见过一整个繁星璀璨的夜晚。
在睁眼梦就失温的惆怅里,白云温顺,黄昏掉落只言片语。桑葚熟了,有些晚荷在霞光里生长莲子,螃蟹悄悄地红起来。离乡的年月,石堰塘逐渐成为拗口的生词,成为笔记里干瘪的情深,成为后院雨后被鸟啄烂的桃子,成为许多风过花落的憾事。
我试着沿着父亲的足迹去触摸,在一个傍晚,太阳落坡,父亲与大伯扛着拌桶走在前面,我在后面捡拾掉落的稻谷走了好远好远。在那个傍晚,我弯下的腰,骨头磋磨的那刻成为若干年后身体的疼痛,时刻提醒着。
这片生养的土地,是一位圣者,她隐身于我的欢乐,出现在落寞。
她让我有一地安息,让我踏实地远去和随意地归来。
2024年07月31日
新闻内容
第A4版:
要闻
石堰塘的春秋
○ 李俊蝶
备案号:渝ICP备08002051号 |